作者|等等
《枭起青壤》在超点完结日的热度跌回了仅次于开播日的新低,播放量也被后来居上的《大生意人》反超并且日渐拉开距离。
以迪丽热巴的流量级别、加上尾鱼“超大IP”的招牌来看,这样的数据表现实在不达大部分人的预期。
与此同时,尾鱼小说的书粉也没闲着,飞速翻出《枭起青壤》导演田里在八年前拍《河神》时的一段采访,文字中“尊重原著是在害人”如同一颗延时炸弹,刚好在剧版遭遇质疑的当口“砰”地炸开。书粉怒火高涨,网友判断混乱,评论区从“你没懂原著”吵到“你就是不尊重原著”,再吵到“你拍的根本不是原著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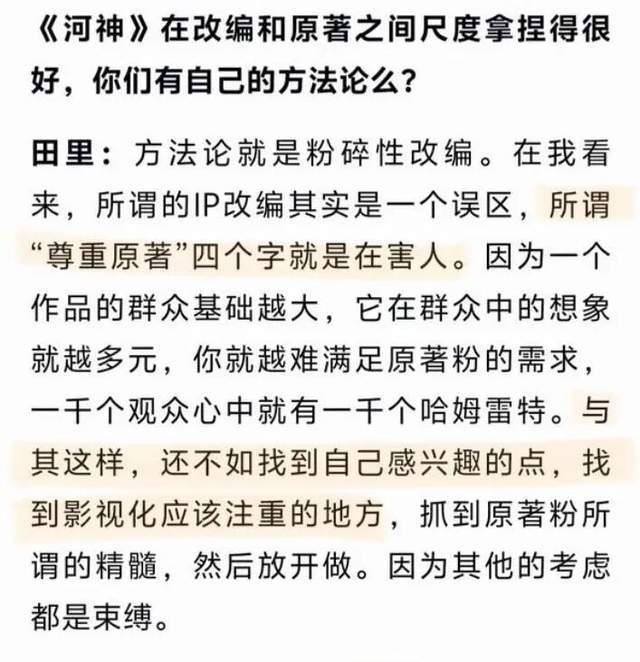
《枭起青壤》导演田里八年前的采访
如果只看这一轮骂战,你甚至会以为尾鱼小说是那种“读者自己都看不懂”的小众怪谈,可事实恰恰相反,尾鱼在网络文学世界可以说是“铁盘”级别的存在,书粉忠诚度极高,长尾效应也足够稳,甚至到了她写什么、读者就追什么的程度。读者执迷于她笔下的东方志怪世界观和诡谲氛围,恨不得有人能把她营造的“民间神秘感”和“精怪味道”完整拍出来。
可是,一旦进入影视化,情况立刻像被诅咒似的,《怨气撞铃》剧版被书粉自嘲“看了怨气大到想要撞铃”,《西出玉门》在黄沙中拍得索然无味,《七根心简》被吐槽棚内虚拟拍摄看着廉价,《枭起青壤》眼下也走向同样的命运。尾鱼小说人人觉得“味儿正”,但剧版几乎部部“味儿变”。
是尾鱼的故事太难懂?还是主创太爱“自由发挥”?问题恐怕都不是一句话可以解答,就好像娱乐资本论(id:yulezibenlun)从影视从业者和书粉的口中听到了不同的答案。


“文化认同”的消失,“反逻辑”的改编
“尾鱼剧的世界观好难懂……”
网友小帕向小娱直言,自己没有看过尾鱼小说,但因为看过剧版《司藤》,又听说尾鱼小说充满志怪,所以一度非常期待可以看到翻拍后的中式奇幻剧。当她发出对故事世界观的感叹时,或许也说明了改编的问题所在。
书粉鸭鸭认为,《枭起青壤》给人的第一重失落,是它把尾鱼作品里那种“越诡异越清晰、越复杂越有条理”的感觉,拍成了另一套“越解释越混乱、越直给越陌生”的世界。尾鱼世界观的复杂虽然在于它需要通过故事推进徐徐铺开,但小说本身用了中国实际的地名和《山海经》等传统书籍里耳熟能详的精怪称呼,这是长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的“根”,是你只需要跟着走就能看懂的结构。

“可能是为了审查原因,剧版把这个和中国人血脉相连的文化根源的标签都改掉了,就像自己关掉了唯一让观众快速进入故事的那扇门。”鸭鸭所指,正是小说里那些真正能帮观众“迅速抓住叙事逻辑的文化坐标”被彻底换掉了。
一个最典型的例子,就是剧中聂九罗讲述“地枭起源”的那段大篇幅解释。改编剧里,地枭被描绘成“天降陨星后出现的异类物种”,嗜血、残暴、像某种来自地球之外的怪物。这种粗暴直白的解释在影视剧里似乎常见,但对书粉来说就是把尾鱼世界观最关键的底座连根拔起。
原著里的人与地枭,是同源的,都是女娲创造的生命,也同样属于地球。黑白涧不是科幻裂缝,而是女娲亲手划下的两个物种的生死界限。地面以上归人,地面以下归地枭,不是因为天外异兽,而是因为地枭有食人的风险,双方冲突扩大,才被迫分界。也正因为有这层“都是女娲的孩子”的设定,当读者看到地枭的母子情、看到疯刀血脉里的挣扎,会自然地感到心酸,而不是单纯把他们当成怪物。
编剧兼书粉的小青慨叹,“这些东西在剧版里完全没了。观众现在看到的故事,是一个外星怪物与人类的对抗,是一种天降灾害的简单逻辑,这种简化本身没错,只是它完全不是尾鱼的叙事方式。小说里根植着神话的温度,剧版却换成了科幻的冷感,两者的差别大到让熟悉原著的人感到瞬间出戏,没有看过小说的观众也失去了快速进入故事的文化认同。”

被书粉认为毫无中式志怪更像外星生物的地枭形象设计
这句“文化认同“或许就是网友小帕认为世界观复杂的一层主要原因。
而在小青的理解里,比起世界观的改写,更离谱的是“南山猎人”的改写,“剧版把南山猎人写成正义之师,肩负灭枭使命,代代为守护人类而战,听起来既宏大又正义。但原著压根不是这么回事。”
真实的故事里,南山猎人抓地枭不是为了天下苍生,而是地枭可以嗅探到宝物,南山猎人为夺宝抓枭,聂九罗因为三观不合而出走。把“真实的人性”变成“干净的使命”,把“复杂的利益链”变成“宏大叙事”,原著那种“所有角色都活在选择里”的张力,在剧里完全被抹平。
“剧版里洗白南山猎人,聂九罗的出走就显得不想肩负正义使命,很不负责任,女主的立场完全就立不住了。”这也是鸭鸭和小青最为生气的地方,毕竟“尾鱼大女主”素来都是尾鱼小说最有致命魅力的根源之一。

被“男凝”的大女主,被“炒CP”的公路冒险
谈尾鱼改编,影视策划阿水几乎是从《司藤》开始说起,这部当初平台并不看好的A级剧,播出了S级的黑马效果,这也是近几年尾鱼IP备受影视改编追捧的源头。
“从民国活到了现代司藤需要融入现代社会,她拍身份证照被要求卸妆、摘掉配饰、扣好衣领,这个过程中她在极力控制脾气;抓娃娃时被小朋友抢先一步,她也想要,那种不服气的少女心突然跳出来;第一次喝奶茶,她像在吸收一种陌生又好玩的能量,表情从警惕到雀跃,是活生生的生命曲线。”

阿水感叹,这是切实可以让观众感觉到,她真的在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,一个藤妖在试着变成‘人’。”也正因为这些情绪的流动,司藤的骄傲、傲娇、小孩子气、成年人的克制,都在同一条生命线上成立了。
这样的“活人气”,原本在《西出玉门》里可以是另一种面貌呈现。阿水最初对倪妮饰演的叶流西有过期待,玉门关边穿着军大衣卖西瓜的第一幕,让她看到了角色的线条与生活感。然而进入玉门关后,气质突然断裂。超短热裤的造型、从腿一路摇到锁骨的洗澡镜头,让不少观众瞬间出戏。

“尾鱼的女主从来不应该被男凝。”阿水直言,《枭起青壤》里对聂九罗的描述有着类似的视角,比如在小说里用来打破读者对“雕塑家皮肤不好”的刻板印象,所以形容了从事雕塑艺术的聂九罗其实手部皮肤很好,但在剧版改编时却加入了“你的手糙,和脸不搭”的男主的调戏之语,让女性观众大为不适。
而本该和聂九罗形象很贴合的热巴,在剧中却被拍成了几乎只剩下美貌的单薄。原本是书里最有狠劲、最有锋芒的角色之一,每一步动作都应该藏着“疯刀”的危险感,但剧版里妆发的华丽、姿态的端庄,只在提醒观众“她很美”,却没有任何情绪能支撑她“为什么这样活着”。
阿水直接形容,“她是漂亮的,但没有活人味儿。”

当然,比起“被男凝”的尾鱼女主们,真正让阿水困惑的,其实是尾鱼IP为什么总在改编过程中被推往“言情之路”。尾鱼宇宙的底层结构根本不是情感驱动,而是东方奇诡体系下的冒险驱动,它们都绕着同一个神话“母题”展开:女主可以重生。
“尾鱼的神棍宇宙几乎所有女主都有复活的buff。”阿水细数,从司藤到叶流西、木代、聂九罗……青壤土本身就象征着生命循环。“复活”是尾鱼女主的核心密码,是她用东方神话结构包装出来的独特魅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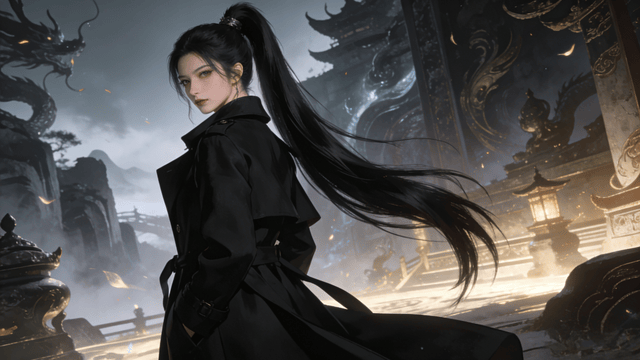
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
可是,一旦进入影视改编,情况就变得非常尴尬。
因为复活的设定,让尾鱼女主天然免疫死亡,而“不会死”意味着冒险中的危机、死亡带来的情感拉扯、角色生死之间的黏度,全都会大幅下降。阿水总结得很清楚,“男女主在冒险中产生情感,本来是依靠生死时刻去建立的。但尾鱼女主不会死,那你要怎么写那种惊险?怎么写情感的紧绷?一下子就没张力了。”这就是尾鱼剧增加感情线的天然矛盾。

问题的关键不只是“男女主好不好嗑”,尾鱼故事的真正魅力在于奇诡、冒险、东方神话,在于那些生长在神秘土地上的陌生生物和陌生命运。阿水甚至觉得,尾鱼的作品更像是“现代聊斋”的坯子,如果愿意把情感线当作点缀,把“人”和“诡”的关系拍透,反而会更立得住。
她以《唐诡》系列“以诡写情”的本质以及《无忧渡》从人心的曲折里长出“聊斋式”的奇诡故事为例,但尾鱼剧除了《司藤》之外,几乎所有改编都像“名场面PPT”,本来可以写成“人在诡中、诡因人生”,结果却被拍成“人影在光里、光影盖住人心”。
“故事的魂没了。”阿水笑言,“你看尾鱼的大部分小说,只能说她的故事很好看、设定很强、文笔好,让人看起来鬼气森森的,但是基本上很难用一句话总结故事。”

阿水甚至认为,如果有导演敢彻底摆脱“炒CP”的执念,尾鱼的“东方志怪”世界观反而最容易拍出差异化。“关键不是谈不谈恋爱,而是你到底想让观众看什么,如果你想看漂亮的人摆造型,那就是现在这样;如果你想看一个诡异但好看的故事,那尾鱼其实给了你非常好的原料。”


尾鱼剧改编困境只是“大作者IP魔咒”的缩影
把尾鱼的改编困境单独拿出来讨论,总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场发生在个体作者身上的意外。但从行业视角往回看,无论是尾鱼、马伯庸,还是更早被奉为“黄金 IP”的东野圭吾,他们的作品在落地影视化时几乎都遇到过同样的难题:小说越成熟、作者声望越高,影视化反而越容易失去方向。
这并不是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必然鸿沟,而是在长期的改编实践中,行业对“大作者 IP”的过度依赖。
最常见的误判,是影视行业把大 IP 当成了一种“安全资产”。无论公司还是平台在购买版权时,往往因为庞大的小说拥趸而默认“故事已经被市场检验过”,于是本能地希望保留更多原著、保住更多粉丝点、保住更多人物关系。然而,越是害怕失去原著,越容易在拆解时陷入停滞,最终呈现出来的,是对原著的“全面保留”与对影视化的“全面妥协”共同叠加后的混杂状态。

更深层的问题,包括大作者 IP 身后的成本核算。以尾鱼为例,她的主流 IP 售价大多落在一两千万区间,这在业内属于相对合理的比例。但到了《龙骨焚箱》,因为是“尾鱼宇宙收官作”,有传闻其成交价接近四千万。这个数字意味着,一个 IP 可能占据制作成本超过10%甚至更多,它把整部剧的创作自由度压缩到了极限,意味着主创要承受更多风险和压力。
同为近年备受质疑的马伯庸,情况亦如是。《长安的荔枝》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在出版端是成功的,它们的读者面广、议题轻巧、风格稳定,改编看似“安全”,但真正落入影视化时,故事的内部张力却并不足以支撑完整剧集。

阿水认为,马伯庸擅长从史料缝隙里拎出一句话,进行十几万字的戏说延展,这在阅读时轻松、灵动,甚至带点少年漫气质,但影视剧需要的是更明确的主线、更深的人性重量和更有节奏感的推进逻辑。因此,哪怕原著再受欢迎,也免不了在影像端被稀释、被打磨,最终呈现的作品往往比小说“更松、更浅、更像一段被拉长的知识段子”。
但平台依旧愿意持续购买这些大作者的作品。原因并不复杂:尾鱼、马伯庸、东野圭吾都拥有被市场验证过的“基础盘”。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张票房保底,一种“不会太差”的保证。
然而,正是这层看似稳妥的“安全感”,让大作者 IP 在影视化的过程中不断陷入悖论:越是确保不会失败,越难真正成功。

因为真正打动读者的,从来不是故事的结构,而是作者独有的“写法”,比如尾鱼的奇诡东方气质、马伯庸的轻戏说历史、东野圭吾的反人性剖析等,这些东西恰恰是影视工业最难完整复刻的部分。当制作方选择“保守改编”时,这些关键气质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。当制作方选择“大胆翻译”时,又会被粉丝指责偏离原著。
于是,大 IP 改编常常会陷入一种奇怪的循环:原著越强,改编越谨慎;越谨慎,越拍不出原著的魅力;越拍不出,越需要明星、大场面去兜底;越依赖兜底,越难回归故事本身。“看起来保险”的改编,最终仍然会变成“高成本的平庸”。
大作者 IP 改编困境或许从来不是“故事不够好”,而是影视工业无法同时满足成本、审查、粉丝、营销、平台上新节奏等多重要求。
也因此,大作者 IP 的真正价值可能与过去十年的想象完全不同,它已经不是低风险的安全资产。当行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,也许平台和片方才能从“高价困境”里走出来,大作者 IP从才能从“改编魔咒”里跳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