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|阿楚
“熬夜是常态,最久的一次熬了两天,中间只睡了两个小时。”
“一部55集的短剧,哭戏就占了50集,演完孩子性格都变得敏感了。”
“第一场戏就是淋雨,孩子整个人都被浇懵了。”
短剧的兴起,确实给家长和小孩更多实现“童星梦”的机会。尤其是今年上半年,萌宝题材甚至成为短剧行业的爆款,主演日薪2000-5000成了一个常态。但在与家长和业内人士的对话中,娱乐资本论也看到短剧小演员行业的另一面。
从入圈开始,家长就要与信息差作斗争,花钱进群看组讯只是第一步。如果没能演到爆款成为头部,后续还需要继续“投资”挂靠演员经纪或者小演员培训机构,获得更多出演机会。
拍摄期间,小演员也很难回避熬夜、淋雨、大哭等“虐身又虐心”的情况,更棘手的是短剧草莽发展期,一些不合逻辑的剧情对小演员的心理造成影响。
不少家长表示,在选剧本时会拒绝有“虐小孩”情节的剧,有少儿不宜情节、台词爆粗口的剧本不能接,有家长甚至不想接有多个小孩的剧,“怕几个小孩在一起吵架”。小演员芊芊的妈妈曾拒绝过一个剧本,因为要求“孩子在KTV卫生间看成人亲密戏”。还有短剧出现女主开车反复撞向自己孩子的离谱剧情。
头部制片人小徐告诉娱乐资本论,在拍摄到一些涉及吵架、霸凌、凶杀等负面情节时,剧组会特别告知小演员“这些剧情都是不对的,拍出来是为了警示大家。”
但更多时候,剧组对小演员的身心健康的关注还需要更多制度上、规则上的约束。
经历了这一系列“磨难”后,短剧小演员还面临着出路不定、未来迷茫的困境,大多数小孩在小升初之后只能放弃演戏,但之前经常熬夜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已无法挽回。
尽管短剧的大量生产造出了更多“童星梦”,但最终这也只是少数人的游戏。
(西西、妙妙、小米、阿利、虾米、小徐都是化名)
#本文已采访九位相关人士,他们也是「娱乐资本论」2025年采访的第359-367位采访对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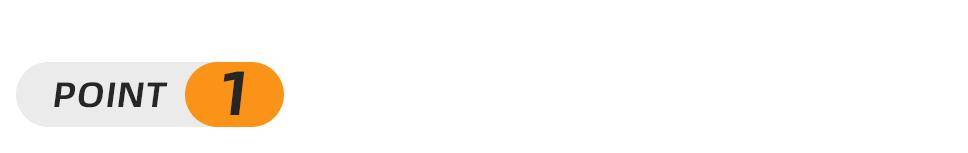
入局先拼“家底”,金钱铺路成常态
小演员的起跑线,藏着家庭资源的巨大鸿沟。
与星二代们可以轻松进入娱乐圈,搭档大明星,演大导演的戏类似,短剧小演员的家长们也常有圈内资源。
演过爆款剧的虾米是从广告圈转入短剧圈的,他的妈妈其实手握“内部资源”,因其亲戚在短剧剪辑公司工作,萌宝题材剧本直接递上门。试戏当天就确定了人选,作品播出后即登顶剧查查热力榜NO.1,至今片约不断,档期常常排满下个月。
对少数手握资源的孩子来说,被经纪人发掘后,几乎不费力气就能成为 “小主角”,再稳步成长为绝对的男女主;但对更多家庭而言,入圈更像一场需要 “家底” 支撑的硬仗。
破除信息差只是第一步。小米的妈妈将孩子挂靠经纪机构的入门费动辄1万至10万,只为挤进能看到剧组信息的微信群。“很多家长交了10万,一个角色都没拿到,机构只说孩子‘资料不行’。”

对于这种情况,家长已习以为常,权当一次教训,这个机构中不了单,再转其他机构,或再掏钱报机构推荐的“保过”培训班。家长的心理焦虑,成了这些小演员经纪最好的“提款机”。
除了金钱,时间与精力的投入也是隐形的 “家底”。短剧小演员的家长至少有一方需要全职陪孩子演戏。
阿利爸爸是一名自由职业者,常常一边处理线上的工作,一边在片场照顾阿利生活。阿利第一部戏是客串角色,当时他的爸爸直接开车从杭州到横店,“剧组是不提供车费和住宿费的,都是自费,但是孩子有机会出演就很开心”。
西西的父母是个体户,疫情期间从四川搬到重庆,爸爸在做工程,妈妈全职帮公司报税,“谁有空谁就陪西西跑组,从重庆拍到全国,行程排得满满当当。”
妙妙的妈妈平时除了在剧组照顾孩子生活,平时也要观看孩子的短剧剪作品发社交平台。
但对于这些小演员未来的去处,更多家长的计划是“走一步看一步”。
想未来往横屏长剧发展?长剧市场留给儿童的角色少之又少,加上入圈的资源壁垒,普通家庭的孩子想进长剧剧组更加困难,且长剧制作周期长,播出时间并不确定,对自身的加成效果并不大。

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
一位业内制片人告诉小娱,他接触到的大多数小演员在小升初后都不接剧了,一方面孩子年龄增长之后“萌感”下降,接戏范围缩小,另一方面,发现童星没有后续可持续的上升路径后,更多家长只是抱着体验生活的态度增加孩子的社会经验。
西西妈妈寄望于“曲线救国”—— “拍短剧就像曲线实现梦想,说不定就被大导演看到”,她总是念叨着“我们自贡出了饶雪漫、郭敬明这样的知名编剧,说不定哪天就有合作机会呢。”但她也深知,这是一场豪赌。
可即便如此,还是会有更多抱着“童星梦”的家庭闯入短剧圈,想在这场游戏里,搏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。

熬夜、淋雨、身体透支
虾米2023年第一次拍戏时即一人分饰两角,原本7天的戏,整整拍了14天,他的戏基本都是夜戏,夜晚出工、凌晨收工,日夜颠倒。转场间隙,他只能蜷在椅子上打盹。

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
拍摄节奏快、一周拍一部是短剧的常态,而短剧小演员也和成年演员一样,熬大夜成家常便饭,这也是采访中家长普遍都提到的、最担心的问题。

娱乐资本论了解到,小演员接戏时默认拍摄时长为一天14h或16h,一旦超时由剧组支付10%超时费。“原先制作方还会因为想减少超时费合理安排时间,现在有的制作方宁愿给超时费都要孩子熬夜把戏演完,恨不得一天24小时连轴转。“芊芊的妈妈表示,最近短剧小演员的需求增多,他们几位腰部小演员的家长联合起来,跟制作方提出不接受超时费,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拍完。
一位短剧制作人告诉娱乐资本论,一般来说,如果一定要熬大夜拍夜戏,剧组会和家长提前沟通,让孩子在白天多休息,尽量保证合理的休息时间。
短剧草莽发展期有各种离谱情节,也可能让小演员遭遇极端的拍摄环境。
小演员西西人生第一场短剧戏份就是淋雨。在原剧情中,主演因为被陷害成“扫把星”被丢弃在大雨夜的山里,瓢泼大雨从洒水车倾泻而下,“孩子整个人被浇懵了”,妈妈记忆犹新。两条拍完,湿透的衣服只能用冷风吹干,紧接着又是第二轮浇淋。而且山上没有热水,只有刺骨的寒风。

古装戏更是夏天噩梦般的存在,穿着厚重的长衫,带着密实的头套,烈日下一烤就是一整天,稍有“话语权”的小演员会直接拒绝,但对更多孩子来说,“有戏拍就不错了”,根本没时间挑拣。
成年人的身体尚且支撑不了高强度拍摄,更何况是抵抗力本就较弱的孩子,他们的身体还在生长发育阶段,熬夜、淋雨、长时间暴晒这些超出负荷的消耗,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当下的煎熬,更可能留下未来的健康隐患。
曾拍过奥利奥广告的小沐晨是一个童模,从3岁开始接广告,小红书主页满是精致的照片和视频。可今年一次拍摄中,她因情绪激动突然晕倒,做了开颅手术。
表面光环下,这些小演员承受着不为人知的压力,而日薪超过家长的小孩,也有可能沦为家长赚钱的工具。

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
台湾童星纪宝如的人生被奶奶掌控,为了让她一直当 “童星” 赚钱、逼她打抑制成长的针,如今 63 岁的她,身高永远停留在 149 厘米。
被称为“年画娃娃”的邓鸣贺6岁开始上春晚唱豫剧,一次演出后确诊了白血病,8岁就在家长的持续”消费“中离世,但是家长为了维持家族“生意”的运转,开始按部就班地培养妹妹接替哥哥的工作。
这样的例子并非个例。曾有一段视频引发全网愤怒,在广告拍摄现场童模妞妞因为动作慢,被身后的妈妈抬脚踢向她的腿部。镜头前的精致可爱,背后是孩子被当作 “摇钱树” 的粗暴对待。
2015年“限娃令” 出台,未成年人参与演艺工作本就成了敏感领域,可随着短剧行业的爆发式增长,对小演员的需求陡增,童星梦看似触手可及,背后的隐患也逐渐显露。

片场催熟、成人剧情,小演员心理健康需关注
小演员阿利的爸爸对拍戏给儿子带来的改变颇为欣喜,上四年级的阿利曾因踢球没天赋而受挫,接触演戏后却意外地顺风顺水,跑组一年多,整个人变得开朗自信。
但像这样因演戏给孩子带来积极影响的案例是少数,孩子在片场的经历,更像一场提前闯入成人社会的试炼。
芊芊妈妈观察到,在剧组待的越久的孩子,似乎变得越“圆滑”和“油腻”,心理以及性格都会受到一些影响。
芊芊拍过一个主角是小太后的短剧,剧中满是阴阳怪气的台词,“拍完之后,她日常说话的时候也常常会冒出类似语句,戏内戏外的情绪变得难以分辨。”
妙妙的变化更让她的妈妈揪心。“连续拍完 50 集哭戏后,孩子的性格变得格外敏感。以前摔倒了拍拍屁股就爬起来,现在却会下意识掉眼泪。”妙妙的妈妈认为,“其实没有什么原因的硬哭是不符合语境的,观众看多了也会累,之前妙妙演的、大家反馈比较催泪的短剧,其实并没有什么哭戏。”

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
更让她心疼的是一次吊威亚的经历,妙妙在现场被威亚磨得腿生疼,拍完后孩子夹着腿走路,她才发现屁股已经磨出血。“不是已经慢了吗?我不想耽误大家。” 六岁孩子的话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,这种超出年龄的懂事,让她第一次认真怀疑:拍戏到底是不是对的选择?
短剧草莽发展期,制作方追求“爆点”和“爽感“,往往会用夸张的情节和恶俗的趣味吸引观众,逻辑不通的剧情,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。
芊芊曾拍摄过一部戏,开场一个女孩直接死在了她爸爸面前,可爸爸却转头就走。饰演爸爸的男主当即向导演提出疑问说不符合逻辑,导演也表示没办法,剧本这么写,只能这么演。
制片人小徐向娱乐资本论表示,“不少家长会对孩子被打、生病去世等死亡的情节比较介意。这个不要说家长,我都介意。”
短剧《守望黎明的曙光》里,就出现了妈妈因不知地上是自己的孩子,而反复撞向孩子甚至将孩子撞死的情节,这样的剧情设置显然不合常理,也会让饰演孩子的小演员留下心理阴影。

更让家长炸毛的是成人内容“擦边球”。
芊芊妈妈断然拒绝过一个剧本,要求小女孩在KTV卫生间目睹“成人画面”。 她认为这类画面让成年人来拍、“让成年观众来看都没问题,但非要加一个小孩站在那里看的情节,我实在接受不了。”

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
“其实现在平台对小孩的矛盾冲突或者伤害镜头审查是最严格的”,头部制片人小徐告诉小娱,随着短剧精品化趋势,平台审核加紧,小演员的相关内容得到了更多关注。小徐表示,拍摄过程中,一旦出出现“校园霸凌”等负面情节,剧组人员会对小演员进行现场引导,“会认真地告诉他们所拍内容是错误的,拍出来就是用来警示大家的。”
还有一些隐性的因素正在影响小演员和家长的心态。
芊芊的妈妈观察到,评论里更多的观众并不关注孩子的演技,更多是从外貌上对她家孩子评头论足,比如 “长得不好看”“不如另一个萌”……她尽量不让孩子上网看到这些言论,害怕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的孩子自我认知。
当小演员饰演反派时,也很容易遭受到更多恶评。某部短剧中,一位小演员演了“心机小绿茶”的角色,评论里不少网友担心“演这样的剧情长大后可能也会受影响。”
小童星们生活在聚光灯下,被各种各样的目光注视着,稍有不慎便成为众矢之的。
北京奥运会上的红裙女孩林妙可,因 “假唱风波” 被推上风口浪尖,后续各种争议接踵而至,舆论的重压最终让她不得不淡出公众视野。这种来自外界的审视与苛责,对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来说,往往是难以承受的重负。
快速发展的短剧行业需要对小演员的心理健康给予更多关注。

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
剧组就像一个浓缩的成人世界,孩子们过早踏入这片复杂天地,在镜头下快速成长,但是这究竟是在铺就未来的星光大道,还是在透支珍贵的童年时光?
在追逐流量与效率的当下,为孩子们构筑坚实可靠的心理安全区,已不再是可选项,而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答题。这关乎的,不仅是少数孩子的当下,更是整个行业未来的健康生态。